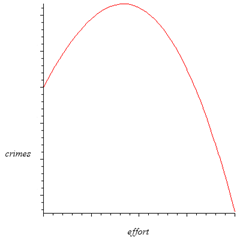清朝的亡国之匾:允执厥中
Submitted by kzeng on Wed, 2010-05-19 12:42
 紫禁城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里悬有一匾,上面是乾隆的御笔“允执厥中”四个字。这四个字很有问题,可以说是亡国之言。按照清朝士人的汉学素养,这样的问题该不难看出,但是却没有人提出异议。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紫禁城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里悬有一匾,上面是乾隆的御笔“允执厥中”四个字。这四个字很有问题,可以说是亡国之言。按照清朝士人的汉学素养,这样的问题该不难看出,但是却没有人提出异议。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乾隆皇帝题写这四个字的本意肯定是要引用的《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十六字真言。宋代理学以义理解经,这十六个字就被认为是尧舜心传,以论天理人欲。明清推崇理学,把这四个字挂在中和殿自然也算是情理之中,但是问题是,这四个字宋儒可以说,士人也可以说,但是唯独皇帝不能说,因为皇帝说这四个字,就意味着禅位,也就是亡国。
这其中原因,简单说起来,是因为《古文尚书》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伪书,《大禹谟》更是东拼西凑凑出来的,这十六个字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古籍里找到原始的模样,譬如这句“允执厥中”,最初的出处大概是《论语·尧曰》: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话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所以在中国的史书里,但凡出现“允执其中/允执厥中” ,大多和禅位有关。譬如,汉献帝禅位给魏文帝的册书:
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
譬如,魏元帝曹奂禅位给晋武帝司马炎的册书:
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
譬如,刘裕矫称的晋安帝禅位遗诏:
其君临晋邦,奉系宗祀,允执其中,燮和天下。阐扬末诰,无废我高祖之景命。
又譬如刘裕的曾孙宋顺帝禅位给萧道成的诏书:
于戏!王其允执厥中,仪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
还有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萧衍的诏书,唐哀帝禅位给朱温的诏书等等,不胜枚举。
当然,也可以争论说禅位并不是“允执其中\允执厥中”的必然含义,但是《汉书·董贤传》里的一个故事说的很明白:
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闳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咸惶恐不敢当,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闳性有知略,闻咸言,心亦悟,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
萧咸因汉哀帝册封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中有“允执其中”这样尧禅舜之文而感到不安,拒绝了董贤父亲为董贤弟弟所求的婚事。这之后,汉哀帝在醉酒时真的说要禅位给他断袖之爱董贤,看来册书的中的行文用典并非无所指。
这个典故也被后世所援引,譬如《宋史·倪思传》:
弥远拜右丞相,陈晦草制用“昆命元龟”语,思叹曰:“董贤为大司马,册文有‘允执厥中’一言,萧咸以为尧禅舜之文,长老见之,莫不心惧。今制词所引,此舜、禹揖逊也。天下有如萧咸者读之,得不大骇乎?”仍上省牍,请贴改麻制。
麻制是唐宋委任宰执大臣的诏命,因为写在白麻纸上,所以称为麻制。倪思看到史弥远拜相的诏命里用到“昆命元龟”四个字,想到了董贤的“允执厥中”,认为皇帝的诏命里出现这四个字是非常不妥的,因为“昆命于元龟”也是禅位之辞。所以倪思上书,请求更改麻制,但是最终却被史弥远罢官。
由此可见,皇帝的诏书中,出现这四个字,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习惯,是非常不吉利的。但是乾隆皇帝却把这四个大字悬在了紫禁城的中和殿上。如果古史官来修清史,写到宣统逊位(事实上也算禅位),恐怕要感叹一语成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