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两天说起清代大臣的谥号,因为太忙没时间,未能尽言,现在有点儿空闲,多说两句。
前两天说起清代大臣的谥号,因为太忙没时间,未能尽言,现在有点儿空闲,多说两句。
美谥有点像时尚,流行的原因有时也不太可考,就像后世以为最荣的“文正”,如果找出它成为 No 1 的原因,大概源头还在司马温公那儿。《宋史·司马光传》上说:
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
文庄。
司马光认为夏竦不能谥文正,而他自己后来又谥文正,大概正是因此,抬高了“文正”的行情。宋人笔记《梁溪漫志》里也提到: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其为厉世之具,深矣。
所以到了清代,一般大臣的谥号,内阁拟定就可以了,唯独“文正”这个谥号必须要皇帝特准,因此清代一共只有八位“文正公”(当然这个数目比起宋代还是算多,正如上面引文所言,宋代有些“文正”的谥号是因为避讳从“文贞”而来的,旧时“贞”、“正”同音,不算真正的文正)。而这八位文正公除了一两位外,大概都未能和宋代的范文正(仲淹)或者司马温公相比,而里面最问题最大的恐怕要数嘉庆、道光两朝的曹振镛了。
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奸良佞之辩,而曹振镛从各个角度来看似乎都不算奸佞之臣:他忠厚、清廉、退让、谨慎。特别是清廉,在乾隆以后贪渎横行的时代,是否清廉几乎成为判定良臣的最重要标准之一。譬如在对待工程的态度上,通常贪官都恨不得皇帝天天大兴土木,以便中饱私囊,而曹振镛却屡次请罢不急工程,撙节糜费。曹振镛是安徽人,世代和盐商有很大的联系,但当朝廷改行淮北票法伤及旧盐商利益时,他也没有护短,而是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支持改革。曹振镛也算是忠厚之人,尽管很多情况下,很难界定圆滑和忠厚,但是他毕竟也没有像传统意义上的权奸一样大肆排挤贤良。
但是正是像曹振镛这样的良臣彻底把清朝拖入了“嘉道中衰”。道光朝一位叫做朱琦御史有一篇《名实论》,认为德行有“乡曲之行”和“大人之行”之分:乡曲之行“曰忠厚 ,曰廉隅 ,曰退让”;大人之行,“在于经国家 ,而安社稷 ,有刚毅之节 , 为人主所惮 ,有深谋远虑 , 为天下长计 ,合则留 ,不合则以义去 ,身之安否 ,不遑计也。世之指擿, 不敢逃也。” 嘉道之间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良臣都是有着“忠厚、 廉隅、 退让”乡曲之行的人,这些人“峨冠博带 ,从容缓趋于廊庙之间 ,上之人固亦深信不疑, 以为渊厚不可以测, 一旦遇大利害, 束手无措, 缄口结舌而不敢言, 所谓忠厚廉隅退让至此遂举无所用 !”
曹振镛就着这样良臣的代表,虽然他生极恩宠, 死备哀荣,但是逐字逐句读《清史稿》、读清代的笔记野史,你根本找不出他到底有过什么事迹。他的一生,倒是真像朱克敬在《瞑庵杂识》里录入的《一剪梅》描述的那样:
仕途钻刺要精工 ,京信常通 ,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 ,一味圆融 ,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 ,莫显奇功 ,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 ,驳也无庸 ,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 ,官远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 ,好也弥缝 ,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 ,妻受荣封 ,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便无穷 ,不谥文恭 ,便谥文忠。
曹振镛把词中的境界发挥到了极致,但问题是清代到了嘉道间并非“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而是危机重重。
重重危机,有些危机已经是很“现代”的问题,譬如美洲白银产量激增(因为使用了新的冶炼技术)和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
美洲白银产量的激增就像现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样,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顺差涌入中国,首先带来的是“汇率”的问题 —— 铜钱和白银比率的问题。
顺治三年的旧制,制钱每十文准银一分,清代一直贯彻这一比率,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文,所有的货币支付,数少时用钱,数多时用银。但是大量白银的流入,导致这样的比例无法维持,康熙六十一年时,钱银比已经涨到七百八十文易银一两,为了维系1000:1的比率,政府只能加大制钱的投放量,康熙间,京局每年铸币大约六、七亿文,到了乾隆、嘉庆两朝,每年大约铸币十五六亿,铸币增长了近三倍。
增加货币投放量的结果是通货膨胀。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讲,康乾间的通胀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对于“康乾盛世”也功不可没,但是持续的通胀亦是“嘉道中衰”的罪魁祸首之一。从康熙到嘉庆间,物价大约涨了三倍,但是国家的正式财政收入却并没有增长。特别是嘉庆帝恪守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许诺,并未增加丁银,物价上涨而赋税未涨。
嘉庆帝始终牢记着“明亡于万历”的祖训,不敢增加税赋,自嘉庆初平定了川陕白莲教起义以来,财政一直吃紧。
同时,国家控制的专卖的盐业也因为实行官方定价(清代盐价提价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哪怕只是一斤涨价一两文钱),不随市场价格浮动而不断亏损,譬如长芦盐厂,到了乾隆末每年亏损折合银七八十万两。
官员俸禄自雍正朝颁行养廉银以来也未在提高,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更加大规模的贪污 ,无官不贪。
到了嘉庆朝,通胀累积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日渐衰竭,地方官员贪污成风。
然后还有人口问题。人口激增,人均土地减少,出现大量无地流民(可以类比现在的失业率),如果政府主导发展工商业,这些流民还可安置,但是嘉庆帝偏偏没有延续康乾间对于工商业的宽松政策,反而禁止民间开矿等等,于是无地的流民民变不断。。。
各种问题累加,社会怪象层出不穷。譬如嘉庆八年,竟出了中国历史几乎空前绝后的平民刺杀皇帝事件(明代的梃击案毕竟针对的还只是东宫)。一个叫做陈德的厨子,因为妻子亡故,岳母瘫痪在床,膝下有一对未成年的儿子,自己又被东家辞退,没有了生计,因为萌发了刺杀皇帝的念头,于光天化日之下在神武门持短刀刺杀嘉庆帝,在场的侍卫们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竟都吓的呆若木鸡,幸亏有大臣格挡,刺杀并未成功。
而面对这样的危机与问题,嘉庆皇帝几乎茫然不知所措,而朝廷重臣曹振镛对于一切问题的答案只是“多磕头,少说话。”。。。。
。。。 其实历史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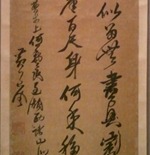 上周周末晚上去林肯中心看芭蕾舞《胡桃夹子》,本来是圣诞节的剧目,图个热闹高兴,但是第二幕在 Land of Sweets 中出现的三个中国人模样的角色确实让人觉得怪异。一男两女。男的戴着斗笠留着辫子,让人想到晚清时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 stereotype —— 又想到,在京剧的剧目中,但凡是牵扯到西方或者北方的“番邦”角色,他们的打扮也多是一副满人的辫子装束,譬如《大登殿》、《四郎探母》等等,所以犹为觉得辫子刺眼 —— 我们用来戏谑番邦的装束却又被被人强加在了我们自己身上,不舒服之余,又觉得有些 ironic ...
上周周末晚上去林肯中心看芭蕾舞《胡桃夹子》,本来是圣诞节的剧目,图个热闹高兴,但是第二幕在 Land of Sweets 中出现的三个中国人模样的角色确实让人觉得怪异。一男两女。男的戴着斗笠留着辫子,让人想到晚清时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 stereotype —— 又想到,在京剧的剧目中,但凡是牵扯到西方或者北方的“番邦”角色,他们的打扮也多是一副满人的辫子装束,譬如《大登殿》、《四郎探母》等等,所以犹为觉得辫子刺眼 —— 我们用来戏谑番邦的装束却又被被人强加在了我们自己身上,不舒服之余,又觉得有些 ironic ...
 前两天说起清代大臣的谥号,因为太忙没时间,未能尽言,现在有点儿空闲,多说两句。
前两天说起清代大臣的谥号,因为太忙没时间,未能尽言,现在有点儿空闲,多说两句。 紫禁城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里悬有一匾,上面是乾隆的御笔“允执厥中”四个字。这四个字很有问题,可以说是亡国之言。按照清朝士人的汉学素养,这样的问题该不难看出,但是却没有人提出异议。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紫禁城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里悬有一匾,上面是乾隆的御笔“允执厥中”四个字。这四个字很有问题,可以说是亡国之言。按照清朝士人的汉学素养,这样的问题该不难看出,但是却没有人提出异议。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