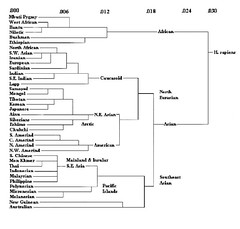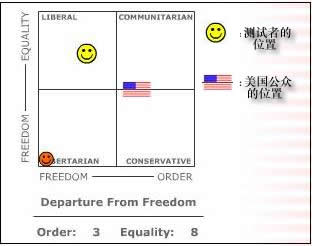呵呵,看到一捆人在讨论鸦片,插个空,说一下清朝末期成功的禁烟运动与之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块疮疤,也是中国近百年来耻辱的标志。1836年清廷关于鸦片问题曾经有一次著名的辩论。这次辩论中有三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者严惩。第三派以大学士穆彰阿为首,既反对弛禁也反对严禁,主张维持现状,这派人从鸦片贸易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故有此说,所以是三派人中最卑鄙的。抛开第三派的意见不说,只前两派就争吵了两年多,后来“严禁派”胜出,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便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从此以后鸦片为祸半了个世纪,直到清朝晚期才再次成功的禁烟(这次成功被后来的辛亥革命破坏了,直到1949年才再度恢复)。但是有趣的是,清朝末年禁烟成功的原因正是被动的采用了许乃济提出的策略。
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在西方,“主权”这一概念在200年前已经形成,到了鸦片战争前已成为惯例。但对于那时的中国来说,主权却是新鲜事物,中国并不理会或是尊重别国的主权,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蛮夷之地的国家理应对中国称臣纳贡,并无主权平等一说,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是比较霸道的,譬如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派出了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此人到了中国后自以为是英国的官方代表,希望会见广东地方当局的官员。但是广东的地方官仍然像对待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一样,拒绝会见律劳卑,让他去见中国洋行的行商。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两广总督便下令“封舱”停止对英贸易。林则徐的禁烟其实也差不多,单方面的给出一个最后通牒,然后禁烟,并没有和英国展开正式的官方贸易会谈,通过协商解决鸦片的问题。当然,在那时即便是协商了,也未必能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鸦片问题的最终解决却恰恰是中英双方通过谈判,签订条约禁止鸦片贸易的。
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目大幅度增加,1863年鸦片进口7万箱,1879年进口103000箱,但是从1880年起,鸦片的输入开始下挫,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本地鸦片的产量大大增加,并逐渐占领了国内市场(如许乃济所预料的那样)。以1900年为例,进口自英殖民地马尔瓦的鸦片613两一箱,印度巴塔纳的鸦片639两一箱,印度巴纳拉斯的646两一箱,波斯的284两一箱(质量很差),土耳其的500两一箱,而四川产的只要327两一箱,云南产的360两一箱,江苏产的400两一箱。特别是后来中国自产的鸦片在质量上并不比外国进口的差,国内市场开始青睐自产的鸦片,“国货”占领市场。
事实上,从英殖民地进口的鸦片价格本来也没有那么贵,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缴纳的关税和厘金比较多。《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可以对每箱进口的鸦片征收30两的关税(事实上,根据《天津条约》的Rules of Trade, Rule 5, Subsection 1,中国可以单方面提高鸦片的关税,甚至到通过关税禁止鸦片进口的程度,但是中国在那时自然也不会那么做),随后根据《烟台条约续增条款》又对每箱征收80两的厘金。英国的鸦片一到岸即由海关封存,在提货时需缴纳30两关税和80两厘金才能提走,也就是说英国的鸦片平白的就贵上了110两。另外还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因为根据条约规定,英国的鸦片只能在通商港口贸易,并不能由英商带入内地,也不能在内地建仓库大量储存,所以鸦片经过中国商人运到内地价格又要高出很多,而本地产品的成本又相对很低,所以英国鸦片无法和中国的鸦片竞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从1873年到1903年,银价与金价的汇率下跌了2/3,使用银本位的中国货币相对使用金本位的英国货币贬值了不少,导致进口的价格上涨,出口的价格下跌,所以外国进口的鸦片的价格就更贵了。更有趣的是,那时中国已经开始从云南向中南半岛出口鸦片了(类似人民币币值偏低,中国产品出口量增加)。
鸦片贸易的衰落为中英正式协商解决鸦片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仍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鸦片贸易仍然为英国带来很多利润,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内建设也需要鸦片带来的税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左宗棠倒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因为鸦片带来的关税和厘金占当时财政预算的5%-7%。但是当在印度调查西藏问题的唐绍仪得知英国对日益衰落的鸦片贸易有放弃的意思后,立即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也当即决定开始与英国协商,国内国外同时禁烟。于是1906年12月,在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的努力下,中英达成协议,从1908年起中国每年减少国内鸦片的产量10%,英国也减少出口的10%,暂行三年。结果到了1911年,中国国内鸦片的减产数量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表,于是1911年5月8日,中英签订《禁烟条约》规定本国生产和外国进口的鸦片在1917年以前完全停止。注意看这个条约的签订时间是1911年5月8日,离清帝逊位已经不远,不知道这是不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国际条约,不管怎样,这个条约算得上一个平等条约了。禁烟也胜利在望。但是随后的辛亥革命打破了一切,虽然英国继续恪守这个条约,对华的鸦片出口逐年减少,但是国内禁种鸦片的努力却失败了。没有了外国的进口,国内的自产的鸦片却大行其道,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秩序再次建立之后。
呵呵,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林则徐和许乃济会怎么想。另,中英《禁烟条约》刊登在《美国国际法期刊》1911年的第5卷第4期上,完全的引用如下: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Relating to Opiu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4, Supplement: Official Documents. (Oct., 1911), pp. 238-243.
在Jstor上可以查到。一般学校的图书馆里也有。一年多前,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无意中翻到这个条约,唏嘘不已。